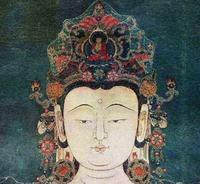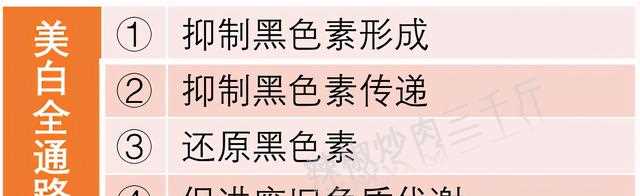女为悦己者容,古往今来爱美是女性的天性,在《木兰辞》中脍炙人口的诗句“当窗理云鬓,对镜贴花黄。”中可见一斑。花木兰是处于南北朝时期的一位巾帼英雄,电影《花木兰》的剧照中所展现的妆容,正是花黄加花钿的复合式妆容。

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唐代侍女绢花图中有关这种妆容的痕迹,只见侍女的额头上先是用额黄描绘上,再在额黄上贴上精美的翠钿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而伴随额黄妆的流行,本文从花黄的历史由来,以及花黄的上妆方法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,说说南北朝最受欢迎的妆容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战乱频繁,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佛教文化得以传播。南北政权在全国各地广修庙宇,大兴寺院,佛教盛行。由此一度掀起百姓崇佛的热潮。一些女子从寺院中的鎏金佛像上受到启发,大胆尝试,用黄颜色把自己的额头染成黄色来增添自己的妆容姿色,这种涂抹额头的上妆方法逐渐从女子中流行起来,为当时最时髦的妆容,并给予它美称——“鹅黄妆”。
“鹅黄妆”不仅深受当时女子的喜爱,就连南北朝南梁简文帝萧纲也对这种妆容颇感兴趣,在《美女篇》中写道:“约黄能效月,裁金巧作星。”这时候的“约黄”便是前面提到的“花黄”。此外还可以称作额黄、鹅黄、鸭黄等。
除此之外,在化妆的方法上也逐渐变化。除了将黄色或者金色的粉末直接把额头涂成金黄色,还有人想出更为精巧的方式,就是把金黄色的纸,剪成星星,月亮,花鸟的形状贴在额头上,这种做法受到追求潮流的女子追捧,慢慢地额黄妆在大众中间开始流行开来。
南北朝佛教绘画
“花黄”属于“鹅黄妆”的一种,兴起于南北朝时期。古代女子化这种“鹅黄妆”一共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染画,就是“约黄”,另一种则是粘贴,就是前面所提到的“花黄”。
染画的两种方式,分别是半涂和平涂。其中半涂法是当时南北朝女子最喜爱的也是最常用的一种画法。首先要准备化妆要用到的物品,古代的化妆品“黄粉”。黄粉的种类有很多,就比如“麝香黄”、“黄金粉”、“松花粉”等。其次,准备一只化妆刷,也就是毛笔,用毛笔蘸抹上黄粉,在前额以眉心为心,涂上一半黄色,再用清水将黄粉推开,向额头两边轻轻晕染。
这种“约黄”的妆容在北齐画家杨子华的《北齐校书图》中有所展现,画里的女子前额上涂有黄粉,自下而上呈渐变色,直到发际线处变淡消失。唐代诗人吴融曾在《赋得欲晓看妆面》中这样描绘:“眉边全失翠,额畔半留黄。”
而唐代女子更愿意选择平涂法,就是将整个额头都涂成金黄色,颇有盛唐的气度,裴虔余在《咏篙水溅妓衣》中用“满额鹅黄金缕衣”来形容这种妆容,额头金色覆盖,每一寸肌肤都发出金黄的光泽,颜色浓郁饱满,没有或深或浅的变化,用色大胆直接毫不含蓄。
额黄除上述两种染画的方式,还有一种粘贴的化妆方式。用金黄色的薄纸剪成各式各样的图案贴在额头上,主要以花朵、飞鸟、月亮和星星为主题。古人的智慧不得不让人感叹,为了使“花黄”可以长时间保留在妆面上,古人发明了一种胶,附在花黄的后面,只要朝着它呵一口气,或者蘸取唾液少许,就能把花黄牢牢粘在脸上,卸妆时用热水一敷,就可以揭下,十分方便。
在此之前,女性的妆容单一,在先秦时期,《楚辞》、《战国策》及《韩非子》等古籍中,有许多关于“粉白黛黑”的记载。女子大多以白粉傅面,使肌肤显得柔软白嫩、吹弹可破。通过这种方式展现自己的青春洋溢,光彩照人的一面,这一时期女子也开始了学会用胭脂和点唇。
到了秦始皇时期,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,女子的妆容风格从原来的追求朴素实用到开始追求个性,突出自身特点的需求,妆容的风格也越发华丽。宫中人的妆容都是“红妆翠眉”,到了两汉时期,女子仍然十分喜欢用粉,不过这一时期,她们会将朱红色的粉傅在前额两侧,当时流行“愁眉啼妆”的打扮。两汉时期,开始逐渐流行画眉,这也是中国古代女子画眉的鼎盛时期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受自由、浪漫、洒脱的文化氛围的熏陶,人们的审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,从追求自然雅致到精雕细琢,当时最流行的妆容包括“酒晕妆”、“桃花妆”、“飞霞妆”等,但是最最经典的妆面还是数“额黄妆”。
这种妆容一直流传到唐代,在卢照邻的诗句中有迹可循:“片片行云著蝉鬓,纤纤初月上鹅黄。”有一个关于上官婉儿的故事,说的是唐代宫廷里流行梅花妆,是因为上官婉儿得罪了女皇惹她不快,女皇便赐她用刀刺伤面部的惩罚,上官婉儿出宫后,为了遮掩脸上的疤痕,就在脸上贴了梅花,没想到反而更衬托出她的姿色。
从这个传说中,可以看出梅花妆的流行是由上官婉儿引起的,阴差阳错没想到“梅花妆”竟成了受人欢迎的妆容。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,古代女子对类似于“花黄”这种妆容的喜欢。
一直到宋朝,这种在额头上上妆的方式还很流行。诗人彭汝励在诗中描述:“有女夭夭称细娘,珍珠落鬓面涂黄。”更为夸张的是,在辽朝时期,在冬天,除了好看还可以保暖的“鹅黄妆”,被契丹族的女子喜欢。她们将黄色粉末直接染面,染面以后肤色金黄,与佛的鎏金的外表极为相似,故又称为“佛妆”。据说,在冬月用括萎(蒌蒿,花淡黄色)涂到脸上,等到第二年春天到来,再把它洗掉。金代的女子,有在眉心作“花钿妆”的化妆习惯。用黄粉涂在额部,一字细眉的造型是蒙古族女子最喜爱的妆容。
“额黄妆”的出现也是一场女妆的变革。妆容的不断变化,代表着女性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,女性更多地开始打扮自己,这也表示她们开始更关注自己,是社会文化的一大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