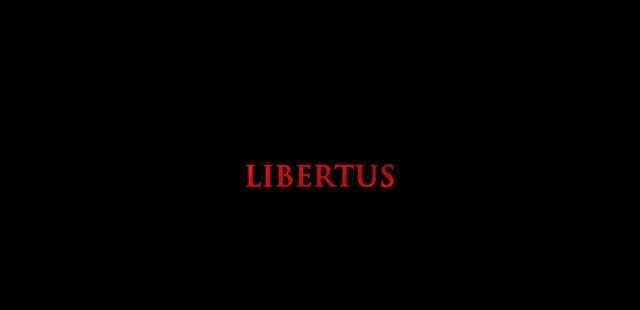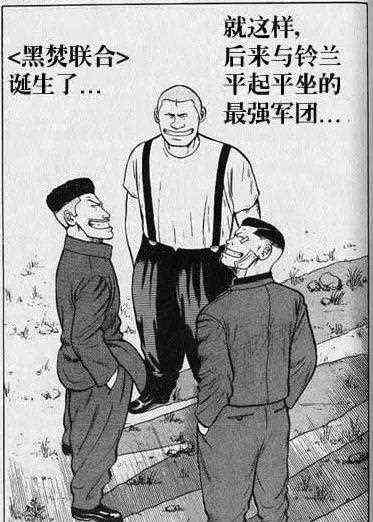人们说武俊英是中国戏曲蒲剧界的名家,绝对是名副其实,众望所归的。称其为“蒲剧皇后”,也当是名不虚传,很是令人信服。
对于名家一词,有关权威的定义为:即在某种学术或是技能方面有着特殊贡献的著名人物。不过在我看来,这样的定义还远远不够,名家还应该是德高望重、德昭于世的杰出代表,否则便不会有像“德艺双馨”这样的溢美之词。而且与技艺相比,我觉得品德当是摆在首位的,诸如德才兼备等等,可见德在人们心目中所处的重要地位。如此而言,武俊英被冠以名家当之无愧。因为在运城,武俊英不仅艺压群芳,而且德性极好,口碑极好。

我与俊英不是很熟,交往也不是很多的,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俊英人生道路和艺术生涯关注的缺失。蒲剧源于我们河东蒲州,一个蒲字便似乎浓缩了我们运城人的乡土感情。可以说我是躺在奶奶怀里听着蒲剧长大的,谁能想到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人,却能够唱出一本一本的蒲剧戏曲,甚至于连过门的音乐都不会落下,可见蒲剧在河东这片土壤上的深入程度。我与俊英素昧平生,完全是因为自己对音律知识和表演艺术的困乏,所以始终是以一个门外汉的眼光,仰视着俊英与她的蒲剧艺术,难以领略到其中美妙的韵味。这对于生长于运城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而言,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缺憾。
说到俊英在蒲剧艺术方面的成就,大家有目共睹,仰若高山不言而喻,单从她所取得的荣誉来看,诸如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、中国第六届金唱片奖获得者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《蒲州梆子》代表性传承人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中共15大党代表、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、山西十大孝星、蒲剧皇后等等称谓,以及雪片儿一样的证书、奖章等等,尽管是冰山一角,却也可窥见其居伟一斑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先生曾赞叹道,“听蒲剧旦角的唱,到目前为止,没有超过俊英的”。这话出自于中国戏剧顶级专家之口,可谓是高屋建瓴,黄钟大吕之音了。
我始终认为,一个人被冠以“名家”头衔的艺术家,不仅仅只是艺术成就的堆砌,更重要的是道德力量的承载。也不仅仅是一种荣誉的赐予,更是一种承当,一种鞭策与奋进的见证,一种对艺术执着追求和对社会无私奉献的褒奖。在我看来,俊英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,其根本就在于她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长期坚守,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,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的懈怠,艺术水准才会这般炉火纯青。也才会被誉为“独占蒲苑第一腔”,彻底颠覆了在人们心中“蒲剧家伙太家伙”的印象,构筑起蒲剧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高峰。
有道是文如其人,事实上演员也是如此。当我走近俊英并真正了解她后,才发现俊英原来跟她的表演风格一样,是一个善与美结合的精灵,德与艺融成的戏魂。在她的骨子里浸透了蒲剧的元素,心血中凝聚着对蒲剧至爱的精华,这也许才是她艺术成功的灵魂所在。用俊英自己的话来说,她似乎就是为蒲剧而生的,当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时,蒲剧就为她铺设下了一条布满荆棘和开满鲜花的道路。从此她就像一位背负绳索的纤夫,又像一名虔诚的布道者,学习,充实,继承,创新,传承着蒲剧艺术,被人们为蒲剧有史以来的里程碑式人物。
都说是梅花香自苦寒来,对于俊英来说更是这样。她虽然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,至今不识简谱,然而却偏偏能够创造出那么美丽动听的腔调来,足足迷倒了整整几代人。我们不反对也不排除俊英的个人天赋因子,但是单凭一个“天赋”就岂能了得,设若如此,我们的人生也就太过于简单了吧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,当我们仰望天空中明星时,不仅要看到它外表的灿烂,更要看到它坚硬的躯体和炽热的内核。在俊英那貌似柔弱的身体里面,蕴藏着她对蒲剧的满腔热情和执着的追求,在她的光环下面,是超出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勤奋与努力。
俊英自从艺以来,蒲剧便融入到了她的整个生命之中,天才加努力,构成她艺术人生的全部内涵。有哲人云,艺术是直觉的产物。我们不容置疑,对于蒲剧艺术而言,俊英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天赋条件,但凡艺术家的开悟和灵感,在她的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各种声乐元素只要通过了她的嗓子,就会成为她个人化的创造,偶有灵感闪现便会豁然开朗,即使无意得之的东西也会更加神妙。尤其是一出《苏三起解》的唱功,悲若空谷幽咽,恋似莺语花底,愤如银瓶乍裂,圆润不流于笨拙,取巧不露出尖俏,创立了与“豪放派”互为补充的蒲剧“婉约派”唱法,于是人们对蒲剧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:“蒲剧好听从俊英开始”。仅此一点,就足以令世人刮目相看了。
对于熟悉戏曲艺术的人来说,都知道唱好容易成派难。言外之意是摹仿容易创新难。虽然俊英生来音域宽、音质厚、音色美,底气足、吐字巧、发声准,自成风格,有着得天独厚的艺术条件。但是如果仅此而已,那么我们也许只会看到一个黙守常规的天赋英才,至多是一个专家说美、观众叫好的优秀演员。设若她再不求进取,贪图安逸,躺在名家的温柔梦中长睡不醒,也许还会在鲜花与掌声面前半途而废,前功尽弃,甚至走上自生自灭的道路。翻检蒲剧百年历史,不乏其例。
令我们可喜的是,俊英在艺术人生中充满着使命感和责任心,始终孜孜不倦地地追求与创新着。她在保持蒲剧韵味传统的同时,纵向继承,横向借鉴,学豫剧的调,借秦腔的音,品越剧的味,跟着京剧学道白,由此形成行腔运字抑扬顿挫、声腔色彩浓淡相间的特色,探索出一种悠扬婉转、缠绵悱恻、平舒圆润、优美动听的新唱法。在发声用嗓、塑造音型等艺术处理上,又无不强烈而微妙地闪现着自己的艺术个性。加之其表演时仪态端庄,气质优雅,台相细腻,自成一格,形成了属于自己的“武派”唱法和“俊英腔”,这无疑是一个奇迹。
人民群众是艺术的土壤,是艺术家的母亲,艺术与艺术家们,只有回归到人民的土地上和母亲的怀抱中,才会有不竭的动力与源泉,也才能够生机勃勃,四季如春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俊英的年龄阅历在变,艺术生涯在变,已从一个不谙世故的黄毛丫头成长为知名全国的艺术家,不过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美德与善良。她伺候九十岁婆婆胜似亲生母亲;她跪在恩师遗像前嚎啕恸哭;她卸妆后连夜赶到瘫在床上的戏迷家里唱“堂会”;她听说临猗有位年轻患者病情严重,便急忙送去两千元善款;她亲自为环卫工人送汤送饭;她与山里乡亲老戏迷亲切合影;她在微信中与戏迷们切磋技艺……
俊英出身于普通百姓的家庭,始终将家乡、将祖国、将时代、将社会作为蒲剧艺术的源泉与动力,把乡亲和观众作为自己的母亲与上帝。她深深地知道,作为一名演员,观众就是你的上帝,就是你的衣食父母,只有你心里装着观众,观众心里才会装着你。事实上在俊英的内心深处还留有一个遗憾:当她听说一位永济籍战士在老山前线作战负伤,是听着她的《苏三起解》离开人间后,就一直想什么时候能够亲自到他的坟前去演唱,以了却烈士的一桩心愿。只是由于种种原因,至今说起来依然是热泪盈眶,成为俊英生命里排解不去的痛。
俊英虽然走进花甲之年,离开了演出一线,不过她的蒲剧情结已刻骨铭心,今生今世难以磨灭了。她培养徒弟,她总结剧目,她要传帮带,将自己“压箱底”的东西,一字一句,一招一式,毫不保留地教给弟子们。她说她业余时间喜欢画梅花,这也许与她的艺术追求有关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梅花以其高洁、坚强、谦虚的品格,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。虽然在严寒中开百花之先,但它却俏不争春,只把春报,待到百花盛开时,它在丛中微笑不语。正如元朝王冕《墨梅》中所说:“不要人夸好颜色,只流清气满乾坤。”值此俊英艺术生涯五十周年之际,借以形容俊英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,当是恰如其分。